暗蓝评《性别打结》丨拆解性别之结需要几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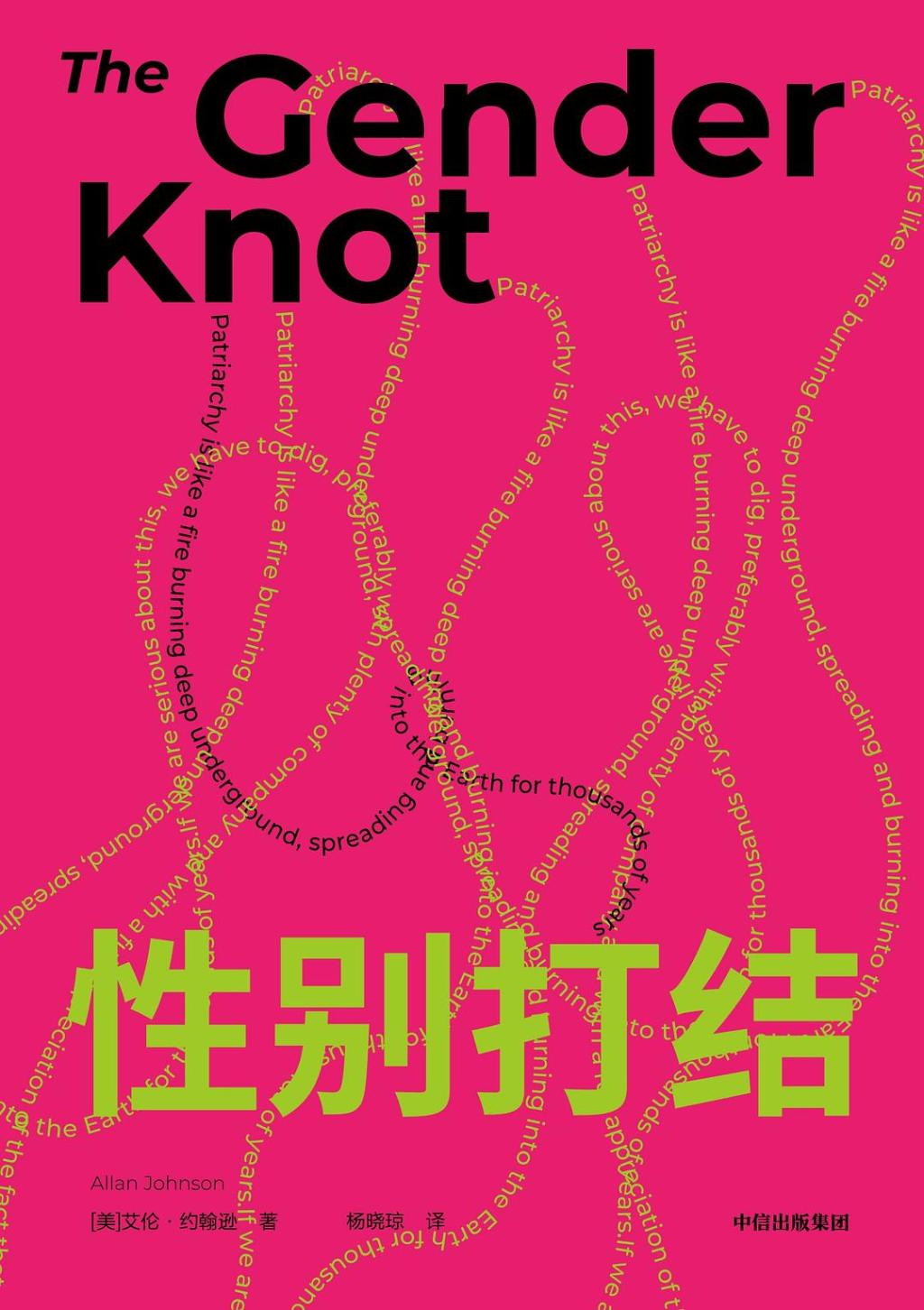
《性别打结:拆解父权制遗产》,[美]艾伦·约翰逊著,杨晓琼译,见识城邦|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9月出版,579页,88.00元
关于父权制,电影《奥本海默》里有一段颇具象征意味的情节。已经开始执行“曼哈顿计划”的奥本海默想要离开研究基地,与情人琼·塔特洛克见面。考虑到计划的“绝密性”,他必须得到军方的安全批准。后者同意了他的请求,但代价是奥本海默必须配合保密要求,即不能与任何“可疑人士”——包括他信任的朋友——联络。当奥本海默终于见到了琼,琼对奥本海默说,“你在我的生活里来来去去,却不必告诉我为什么,这就是权力”。然而等到战后所谓“奥本海默事件”爆发,奥本海默在一场非正式听证会上“受审”,这一事件——权力的赋予——却成了攻击甚至是羞辱他的武器。最后面对妻子“你为什么不反抗”的诘问,奥本海默沉默不语。
或许值得庆幸的是,我们都很难成为奥本海默:拥有绝世的头脑,“奉命于危难之间”——在极端的“例外状态”下被赋予特权,然后随着状态解除、特权丧失被推入谷底。然而令如此命运发生的父权制,实际上至今仍在以相对弱化、日常化的形式困扰着所有人。

电影《奥本海默》海报
“何谓父权制?”在《性别打结》的开头,社会学家艾伦·约翰逊给出了他的定义:“一个遵奉父权的社会,通过男性支配、男性认同和男性中心来促进男性特权。”(第8页)不难想到维系这样一种制度的关键,在于对“第二性”——女性的压迫。然而它还有一个极易被忽略的关键面向,即“它也是围绕着对控制的痴迷而组织起来的”(同上)。作为一名在父权制社会持有主流身份(白人、男性、异性恋)的学者,约翰逊这一研究更大的贡献,便是理清了父权制与他这样并不受其压迫,但受其控制的男性个体之间的关系:父权制“是它,不是他、他们或我们”(第二章标题)——当一个男性拒绝反抗甚至仅仅是去理解父权制,他实际上是将自己的身份与一种控制他的模式等同起来,进而使得自己的存在与之高度绑定,反抗它即是反对自身,而他所遭遇的挫败一定与它无关。然而事实恰恰是一切男性气概带来的灾难皆源于父权制对于男性特权的赋予:想想《白鲸》——在很大程度上,这部名著可以视作对父权制美国“国家神话”命运的预言——中的亚哈船长,倘若他没有将“复仇”想象成自己必须执行的“男性使命”,又怎会执意追逐那“恐怖而不可测”的白鲸,最终招致全船随自己一道覆灭的结局。
经由约翰逊的这一辨析,男性参与到反对父权制乃至女性主义事业的真正理由显然易见。他有必要这样做,并非出于对“她”者居高临下的同情——倘若如此,那他依然沉浸在父权制所期许的“怜香惜玉”当中;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解放他自己。我们甚至还能回答那个聪明如奥本海默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他无法反抗,仅仅是因为“如果你无法想象没有这个游戏的生活,那么除了做符合期待的事情,你是看不到太多其他选择的”(62页)。奥本海默式英雄的一切功绩皆由这一游戏取得:父权制下的男性被鼓励风流倜傥、张扬个性、实现抱负,然而一旦触动了这一体制的控制警报,这些特权便会转化为不检点、不可理喻、不切实际的攻击——恰如它一开始便对女性发动的“预防性审判”,而它正是通过这样的审判将权力从女性身上夺走,然后支出可控的一部分收买男性,并随时准备将其收回。不难看出,在这个游戏中,真正丧失的是“我们”的权力——没有人能在免于恐惧的自由之前提下成为他/她自己——这便是我们受困于“性别之结”的理由,也是拆解父权制遗产、想象另一种可能的意义所在。
为什么会这样——父权 *** 为“最小阻力路径”
与其他女性主义或性别研究著作相比,《性别打结》更大的特色,在于全书以大量篇幅铺设关于理解性别议题极富实践性的社会学进路,而这自然与约翰逊作为一位社会学家长期思考的问题相关:“这个世界充满了如此多不必要的痛苦……以至于除非我们刻意否认或视而不见,否则我们就一定会问‘为什么会这样?’一旦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借助工具来了解问题的走向,并设想如何改变现状。”([美]艾伦·约翰逊,《见树又见林》,喻东、金梓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第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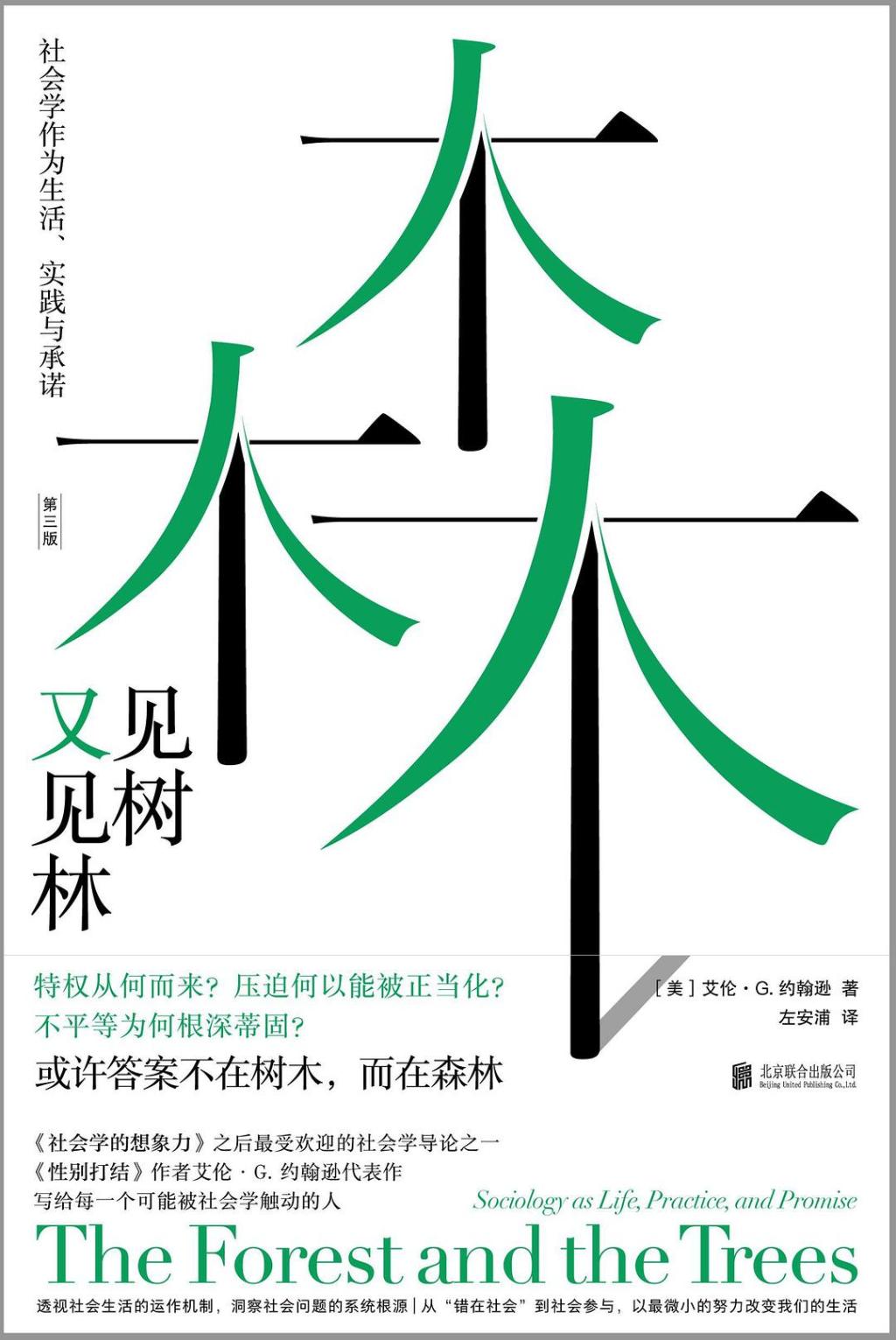
艾伦·约翰逊著《见树又见林》
作为约翰逊致力思考的这一“大哉问”的具体面向之一,在面对父权制问题时,他同样选择了这样的“两步走”。约翰逊在这里使用的工具是社会学概念“最小阻力路径”。尽管他强调作为体制的父权制并不等同于任何个体或群体,但终究还是“我们让社会体制得以发生;当我们参与社会体制时,我们的生活被社会化和最小阻力路径塑造”(55页)。换言之,尽管我们常常以“世上本无路”的套话作为对开拓者的赞美,但更符合社会学意义的表述其实是一条路走的人越多,阻力越小,直至成为唯一的路——哪怕这条路既不宽阔,也不安全:
如果一个社会是压迫性的,那么在其中成长、生活的人会倾向于接受它,认同它并且参与它,把它当成不值得特别注意的常态。这就是所有体制的最小阻力路径,考虑到我们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以及伴随着顺应现状的嘉奖与惩罚,我们很难不去遵循此类路径。当特权与压迫融入日常生活的结构之中,我们无须特意公开施展压迫就能让一个特权体制产生压迫性的结果,正如埃德蒙·伯克所说,邪恶想要得逞,只需要好人什么都不做。(59-60页)
所以好人能做什么?首先便是理解父权制何以成为“最小阻力路径”。于是接下来,约翰逊开始对父权制长期存在的理由进行讨论。尽管人们最容易想到的答案是“本质主义”,即天生的“男女有别”决定了男女在人类社会中的不同分工乃至于地位,但这显然经不起推敲:“如果男性特权根植于男性本质,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男性在为父权制男子气概和他们作为成年男性的生活经受训练时,感到那么痛苦、困惑、矛盾和抗拒?”(94页)而正是在本质主义的矛盾之处,父权制的本质得以显露,“父权制之下的生活安排似乎常常会渗透‘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核心”(同上)——男性通过相信、主张、彼此确认男子气概才成为男性,正如父权制通过时刻主张自己的唯一合法性完成论证循环。
一个通过循环论证确立自身合法性的体制必然是封闭的,而一个封闭体制的维持往往需要一种实现自我循环的动力学。“现代父权制是由控制与恐惧之间的动态关系驱动的,男性通过控制寻求地位与安全,恐惧其他男性对他们加以控制,并将攫取更大的控制权当做唯一的出路”(133页)。有趣的是,在同样致力于启发人们想象超越当下社会模式可能性的作品《人类新史》中,两位作者——大卫·克雷伯和大卫·温格罗——同样提示我们,当下并不完美的社会体制存在暴力支配的循环,“单纯的暴力行为会成为过去,但转换为照护的暴力行为往往会持续存在”([美]大卫·克雷伯、[英]大卫·温格罗,《人类新史》,张帆、张雨欣译,九州出版社,2024年,166页)。最典型的莫过于男性群体通过种种花样也许不同,但必然包含暴力的入会考验、收编“合格者”,并对其提供照护的承诺。而只要将这种“兄弟会”文化放大,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现代国家的隐约身影,“这就是为什么特工成了现代国家的神话象征。拥有杀人执照(并捍卫国家安全)的詹姆斯·邦德集个人魅力、保密性和无限暴力使用权于一身,其背后是一架庞大的官僚机器”(同上,31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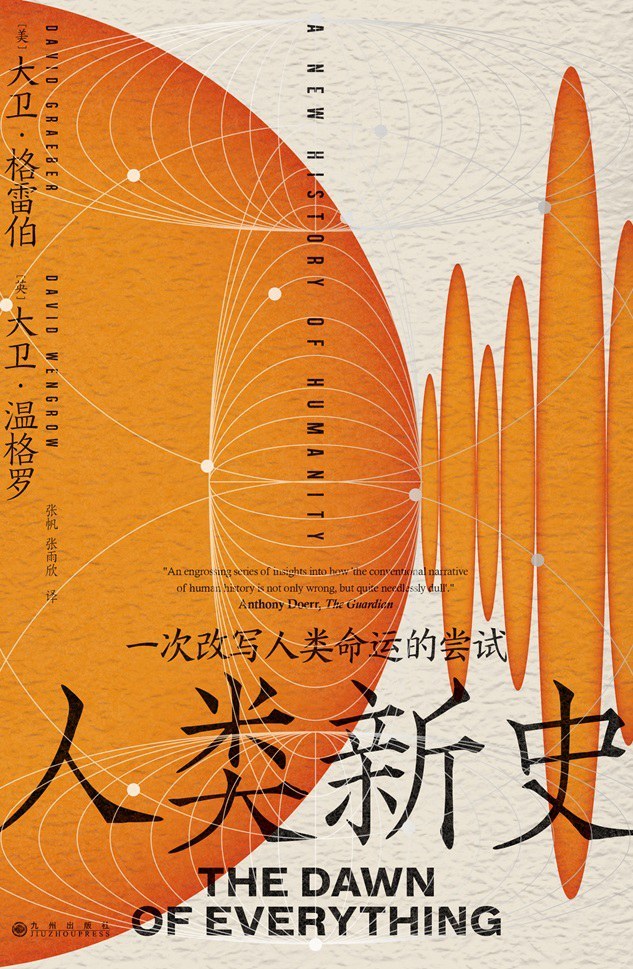
大卫·克雷伯、大卫·温格罗著《人类新史》
在出色地阐释了令父权制得以延续的动力学原理之后,约翰逊继续追问这种“控制—恐惧”的体制何以被人们——主要是男性——所选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男性的连接感比女性的要弱”(133页)。约翰逊在这里诉诸的似乎是一种稍显合理的本质主义,即男性在创造新生命的过程中,其与新生命的连接并不可见,以及身体构造上更容易无视自己的身体,“这让活着变得容易,仿佛人有可能脱离这样的节律,这是克服、超越并最终试图控制自我以及其余作为他者的一切的之一步”(133-134页)。
我们其实并不确切知道一种本质主义是否会比另一种更高明——男性对自我的疏离倾向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同样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然而这种疏离的确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父权制足够稳固的时期,大多数男性尚能通过对女性的支配获取充分的支持。然而随着父权制不再稳固、社会经济条件发生剧变、女性自我意识不断觉醒,到今天因丧失外部支持而陷入绝望甚至走向极端的男性案例越发增多。日本匿名论坛2ch创立者西村博之将这一群体概括为“无敌之人”,这一概念得到临床心理医师斋藤环的肯定。在后者看来,导致“无敌之人”成为一种男性特定症候的关键即在于男性更容易接受压迫性的制度结构,“责任在你自己,你痛苦是因为你自己不行”([日]斋藤环:《自伤自恋的精神分析》,顾小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1月,第16页),进而封闭自我,以自伤的方式寻求自恋的逆向实现,直至难以支撑,造成对自体或他者的暴力伤害。对此斋藤环的建议是自体需要尽可能“与环境或关系之间建立起一种能支撑自体的关系”(同上,182页)——这一建议恰恰与父权制对男性的要求“靠自己”背道而驰。
“主宰者的工具永远拆不掉主宰者的房子”——拆解父权制的女性主义进路
到这里我们已经发现,父权 *** 为一种体制不仅压迫女性,同样也对男性有害。然而正是因为父权制许诺了“照护”的特权,使得男性趋之若鹜,才导致它最终固定成为“最小阻力路径”。或者我们可以用“主宰者的工具永远拆不掉主宰者的房子”这一格言重新理解“屠龙少年”的故事。纵然少年能够识别“控制—恐怖”的封闭循环戕害了自由意志,然而当他完成了屠龙大业,他并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替代选项,只能等待盖茨比式的结局再度降临——“于是我们拼尽全力逆势向前,最终回到了过去”。
为了另觅新路,约翰逊开始探讨女性主义,因为女性主义者似乎天生可以对父权制的诱惑免疫——然而这里仍有例外。实际上“主宰者的工具永远拆不掉主宰者的房子”这句话,本是黑人女性主义作家、活动家奥黛丽·洛德对于一些女性主义者试图沿用父权制权力工具(压迫、歧视、基于等级秩序的“自由主义”)的批判(见Audre Lorde,The Master's Tools Will Never Di *** antle the Master's House,Penguin Classics,2018)。约翰逊延续了这一讨论,指出日后以娜奥米·沃尔夫为代表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分化产生的权力女性主义——“可以利用父权制形式的权力与支配来清除父权制”(212页)——存在根本问题,即“沃尔夫所关切的不是拆除主宰者的房子,而是如何破门而入”(213页)。换言之,这一类女性主义者并不反对“屠龙少年”的故事继续重复,只要求把“少年”换成“少女”,或是男女各半的“政治正确”。
权力女性主义渴望接替父权继续其运作,而其源头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根本问题则是“很少谈及父权制如何组织竞争性的男性同盟关系和对女性的压迫,所以它的关注点只落在压迫造成的结果,而没有检视产生压迫的体制”(214页)。约翰逊再一次以他作为社会学家的观察,要求人们“见树又见林”,“在父权制条件下参与世界的自由,只是非父权制的选项被父权文化所隐藏时的自由”(同上)。基于此,约翰逊更赞同将矛头对准父权制的激进女性主义,然而也正是因为其目标明确且杀伐果决,“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在主流当中几乎是看不见的,除了偶尔有一些更具挑衅性的表达被摘录和曲解,或观点被断章取义”(223页)。
与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同样看到了问题关键的还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版本的女性主义认为今天女性所受的压迫更多与资本主义的阶级动力学相关”(227页)。在约翰逊看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局限在于没有看到父权制影响的全面性,而仅仅是“利用他们最为熟悉的框架,将男性特权塞入一个相对狭窄的资产阶级关系的框架中”(229页),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是反对父权制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这的确是重要的发现”(同上)。他们的发现其实不止如此,一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如上野千鹤子其实已经开始尝试寻求女性主义与“资本主义—父权制”语境的脱榫。“女权主义者在经历了一系列尝试之后,他们才之一次收获了男性字典中没有的概念……当‘男性所做之事可以用女性的语言使之相对化’这种行为成为可能之时,处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中的女性经验才可能找到另一种选择”([日]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邹韵、薛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246-247页)。
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批判产生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父权制不仅关乎性别,而且与社会生活的最基本方面紧密相关”(230-231页)。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批判其实已经与约翰逊的观点基本重合,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流派的女性主义并非泾渭分明,这或许会让人想到艾丽斯·沃克在其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中经常出现的意象“拼布被子”——包容、暧昧,同时又无比坚韧且日常可用。实际上,女性主义与父权制的根本不同,即在于它绝不是时刻主张自己唯一合法性的体制,而是驱散此类经由循环论证生成之阴霾的一线光明。“一旦我们接受了父权制存在的现实,我们就打开了一扇单向度的门;一旦我们穿过这扇门进入另一头,女性主义就是我们弄清楚自己身在何处及今后要怎么做的最光明的希望。”(182页)
日常的,太日常的——想象“时间恒常”
然而,也仅仅是希望。父权制的日常荼毒实在太深,于是拆解它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即便我们跟随约翰逊的论述完成了“两步走”——理解了问题的走向,并且掌握了改变现状的工具——我们也只能回到日常,逐一面对复杂且厚重的父权制意识形态(“意底牢结”)枷锁。于是在《性别打结》的后半部分,约翰逊开始具体剖析父权制的日常表现。从流行文化(“许多人抱怨《末路狂花》中的反派角色让男人显得很恶劣……看来我们有一套双重标准:只有当反派角色为强调其他男人的英雄主义而服务时,将男人刻画成恶棍才是可接受的”[253页])、财富神话(“尽管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另一些人完成的……我们被告知,唐纳德·特朗普‘建造’了特朗普大厦,就像世纪之交的强盗大亨们‘建造’了铁路和钢铁厂”[263页]),到男性对于性的困惑(“他们搞不清楚虐待的性与非虐待的性,分不清什么是性骚扰,什么不是性骚扰……父权制鼓励男人切断所有把自己当作肉身化的性存在的感觉,男性异性恋行为成了男人身体以外的某种东西”[275页]),再到关于暴力、战争与国家霸权迷思(“美国故事的关注点不仅仅是男人,而且是男性视角下的国家力量、自豪感、优越感和例外性,是支配世界和无拘无束行事的自由和权力……把男性暴力当作美国国家意志的工具以及伟大国民性的标尺这一观念,几乎始终占据主流”[426-427页])。
至此,对父权制更好的譬喻,其实并非绳结,而是本书开头便给出的那棵“父权制之树”(32页)。它的根系——作为核心原则的对控制的痴迷、男性支配、男性认同、男性中心——已然太深。值得庆幸的或许是经由本书,我们得以确认自己的角色:我们是身不由已的叶子,生来便长在这棵树上,“我们无法避免参与父权制。从我们来到世上那一刻起,它就被传给了我们”(同上);然而“我们远远不只是被动的树叶”(33页),因为我们可以选择以何种方式参与其中。
果真如此吗?尽管约翰逊对我们被迫接受的这份“父权制遗产”做出了精彩的剖析,也对我们可能采用的改善其影响的女性主义工具进行了介绍,但他其实未能对于“拆解性别之结”给出有效方案。到本书最后,拆解工作也只能化作日常实践,“当我们公开放弃一条最小阻力路径,我们就增加了走在这条路上的其他人的阻力,因为此时他们必须在他们的选择和他们所见的我们的举动之间进行调和”(447页)。同时约翰逊鼓励我们像婴儿学习“物体恒常性”——看不见的物体依然存在——那样,想象一种“时间恒常性”,“即便我们未必能看到,有意义的变化也会发生”(442页)。
约翰逊的方案令人敬佩,但终究有些无力。“性别打结”的关键,也许还是在于性别。父权制强行定义(doing)男女有别,这是其分化人群,促使一群人要求自身支配、控制另一群人的之一步。所以与其考虑日复一日地试图解开性别之结,我们为何不考虑朱迪斯·巴特勒的建议,“消解”(undoing)性别这团乱麻?实际上,约翰逊注意到一个问题,“2%-3%的婴儿出生时的身体特征(包含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并不能清晰地归入一种或另一种性别……在只承认两种性别的文化中,父母通常感到不得不对此做些什么,从杀婴到通过手术给婴儿指定一种性别,都是他们可能采取的措施”(37页);而巴特勒则曾经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的一个极端现实案例,即“大卫·莱恩事件”。大卫天生拥有XY染色体,八个月大时因医疗事故导致 *** 被烧伤。他的父母接受了医生的建议,决定为大卫“指定”一个新性别,让他接受了性别再造手术,并把他当作女孩抚养。然而很快,大卫开始拒绝自己的女孩身份,开始寻求以男孩的身份生活。性别身份的反复困扰了他一生——大卫最终选择在三十八岁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巴特勒将这一案例看成一个“变性寓言”,“可塑性是用暴力手段强加于人的,而自然是人为引发的”([美]朱迪斯·巴特勒,《消解性别》,郭劼译,岳麓书社,2024年9月,92页)。换言之,任何一种性别身份,都只是表明我们“只会在我们的知识的边缘表达自己”(同上,104页)。更为开阔的前景,在这里不言自明。
或许我们还可以回到电影《奥本海默》。在影片中,琼·塔特洛克曾建议奥本海默不要伤害那些真正理解你研究的人,“有一天你会需要他们”。尽管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奥本海默不以为意,但最终还是“科学家同盟”挺身而出,阻止了“体制”对这位天才的进一步迫害。面对注定无法一蹴而就实现扭转的日常困局,在历时性层面想象美好未来一定存在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或许还是在共时性层面寻求更多的“自体支持”——对世界持有相同理解的人,才有可能构建同样的未来。